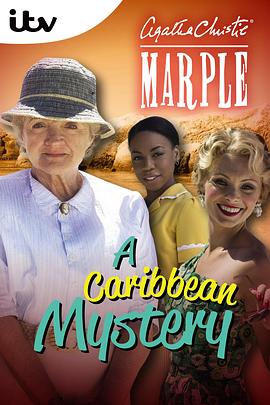- 1.007之霹雳弹[电影解说]已完结
- 2.NBA 马刺vs森林狼20240228已完结
- 3.德甲 弗赖堡vs法兰克福20240218已完结
- 4.86 -不存在的战区- 第二季 86―エイティシックス― 第2クール12集全
- 5.青梅竹马绝对不会输的恋爱喜剧全集
- 6.疯狂希莉娅HD
- 7.孤独的美食家 第二季已完结
- 8.再见妈咪1986HD
- 9.喜气逼人HD
- 10.失魂客栈HD
- 11.陶宝萍的幸福生活HD
- 12.大人物2011HD
- 13.脂粉市场1933HD
- 14.理查三世:看不见的故事已完结
- 15.亲朋密友已完结
- 16.永生之战HD
- 17.恐龙飞车HD
- 18.神奇的费曼先生HD
- 19.欢迎光临千岁酱已完结
- 20.梦王国与沉睡的100名王子 short已完结
明清小说评点家们早已注意到《金瓶梅》写“世情”、“人情”的特点,
如“读《金瓶》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饮,以消此世情之恶”、“《金瓶》处处体贴人情天理”(1);
《金瓶梅》“说得世情冰冷”(2)、《金瓶梅》“深切人情世务”(3)等。
但作为一种小说类别,“世情小说”(人情小说)这一概念则来自鲁讯先生。
如前所述,鲁迅先生对小说类型的划分以及具体作品的归属等问题都有进一步思考的可能和必要;
或者说,鲁迅先生对小说类型的划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的意义。
我们正是借鉴这种方法,将《金瓶梅》等主要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从世情小说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类”来进行考察研究。
小说类型只是假定性的概念,没有固定性和绝对性,而且类与类之间还存在着“中间地带”。
在“导论”中已说到,我们无意也不大可能清晰地界定明清浩如烟海的世情小说中哪些是家庭小说,哪些不是。
但是,作为较典型的家庭小说,还是应该具有基本的“类型”特征。
作为长篇“家庭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奠定了这一类型的基本模式,为后来者提供了参照的坐标。
从“家庭小说”这一角度,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金瓶梅》模式”。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一、以琐碎的笔墨描写日常生活
《金瓶梅》直接继承了宋元话本描摹世情的传统,又在结构上受到《三国演义》等长篇白话小说的启示,其开创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相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而言,它将目光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转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
相对于描写“世情”的宋元话本小说而言,它将情节内容相对简单的短篇扩展成为内容丰富的长篇,一般文学史比较关注前者。
“扩展”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以琐碎的笔墨不厌其烦地描写日常生活。
袁中道《游居柿录》说到《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
说《金瓶梅》只是“逐日记事”自然只是一种推测和夸张,但是,说它“琐碎中有无限烟波”却是的评。
中国古典小说本来以“说故事”见长,可是,《金瓶梅》对这一传统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它是“隐大段精采于琐碎之中”(4)。
作者自己认为,他所写的不过是“一个风情故事”(第1回),全书借鉴《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情节框架,安插一个暴发户家庭在“大约三五年间”(5)迅速兴盛又迅速衰败的故事,而故事的焦点是男主人公西门庆与他的宠妾潘金莲及其他众多女性之间的“风情”。
在简单的故事框架中,填充的是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
这里,不妨随机抽取几例。
第十五回,写潘金莲和吴月娘等一起于正月十五去李瓶儿家看灯市:
吴月娘看了一回,见楼下人乱,和李娇儿各归席上吃酒去了哩。惟有潘金莲、孟玉楼同两个唱的,只顾搭伏着楼窗子,往下观看。
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显他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马镫戒指儿。
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儿,把磕了的瓜子皮儿都吐下来,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嬉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看那家房檐底下挂了两盏玉绣球灯,一来一往,滚上滚下,且是倒好看。”
一回又道:“二姐姐!你来看着对门架子上挑着一盏大鱼灯,下面又有许多小鱼鳖虾蟹儿跟着他,倒好耍子。”
一回又叫孟玉楼:“三姐姐!你看这首里,这个婆儿灯,那老儿灯……正看着,忽然被一阵风来,把个婆子儿灯下半截割了一个大窟窿,妇人看见笑不了。引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挤匝不开,都压 儿。
这一段话写潘金莲观灯的情形,没有情节发展,只是通过一些行为细节和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这时,潘金莲进西门府不久,在几位妻妾之中最为得宠。
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这时节,“她毫无心术地炫耀她的美,在她欣赏这街头灯景的欢乐中,还保有一个孩子纯真的天机,这种纯真以后就很少表现了”(6),这里一连串的“姐姐”与她后来越来越显露的“单管咬群儿”的个性的确具有对比性意义。

潘金莲画像
第二十三回写吴月娘等在李瓶儿房里吃酒玩牌,惠莲趁机在月娘房里与西门庆偷欢,然后再来到牌桌边:
这惠莲在席上斜靠桌儿站立,看着月娘众人掷骰儿,故做扬声说道:“娘把长幺搭在纯六,却不是天地分,还赢了五娘。”又道:“你这六娘骰子是个锦屏风对儿。我看三娘这幺三配纯五,只是十四点儿,输了。”被玉楼恼了,说道:“你这媳妇子,俺每在这里掷骰儿,插嘴插舌,有你什么说处!”几句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飞红了面皮,往下去了。
惠莲和《红楼梦》中的晴雯一样,属于“心存奢望的伶俐女子”,身为下人却喜欢在其他下人面前“非份地表现自己高人一等”(7)。
她像书中其他许多女性一样,企图通过与西门庆的私情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与王六儿和如意儿等人不同的是,她天生聪慧美丽而又莽撞、争强好胜,一与西门庆私,即忘了自己卑微的身份,自觉不自觉地一再与“主子”比高低。
这一次,她竟然逾越界限地教训吴月娘和孟玉楼掷骰子,“故做扬声”或许与“偷情”之后的慌乱情绪有关,更主要的还是自比于主子的心态流露。
孟玉楼“有你什么说处”的斥责,将她从梦境中唤醒,所以红着脸“往下去了。”
这一段描写同样不是“情节”而是琐事“细节”,与故事的发展关系不大,却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心理。

《金瓶梅》连环画 · 宋惠莲与西门庆
第五十八回写潘金莲因怀妒忌而故意打狗打秋菊来惊吓李瓶儿的孩子:
潘金莲吃的大醉归房。因见西门庆夜间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早晨请任医官又来看他,都恼在心里。
知道他孩子不好。进门,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躧了一脚狗屎。
到房中叫春梅点灯来看,大红段子新鞋儿上,满帮子都展污了。
登时柳眉剔竖,星眼圆睁,叫春梅打着灯,把角门关了,拿大棍把那狗没高低只顾打,打的怪叫起来。
李瓶儿那边使过迎春来说:“俺娘说:哥儿才吃了老刘的药,睡着了,教五娘这边休打狗罢。”
这潘金莲坐着,半日不言语,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开了门,放出去了;又寻起秋菊的不是来,看着那鞋,左也恼,右也恼。
因把秋菊唤至跟前,说:“论起这咱晚,这狗也该打发去了,只顾还放在这屋里做甚么?是你这奴才的野汉子,你不发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双新鞋儿,连今日才三四日儿,躧了恁一鞋帮子屎。知道了我来,你与我点个灯儿出来,你如何恁推聋妆哑装憨儿?”
……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拿过灯来,教他瞧!躧的我这鞋上的龌龊。我才做的恁奴心爱的鞋儿,就教你奴才糟蹋了我的。”
哄得他低头瞧,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揾着搽血。
那秋菊走开一边,妇人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
教春梅:“与我采过跪着。取马鞭子来,把他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乱打了不算。”
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妇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点般鞭子轮起来,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
那边官哥儿才合上眼儿又惊醒了,又使绣春来说:“俺娘上覆五娘:饶了秋菊,不打他罢,只怕唬醒了哥哥。”
潘金莲对李瓶儿的请求置之不理,直到“打勾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起来。
又把脸和腮颊,都用指尖掐的稀烂”,而李瓶儿只能“双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颊痛泪,敢怒不敢言”。
潘金莲母亲看不过去出言相劝,也挨了她一顿臭骂。
从刘大杰、鲁迅、吴晗到徐朔方、章培恒、黄霖、张俊等诸位先生无不称道《金瓶梅》对人物和情节的真实性描写,而在所有的评论中,鲁迅先生的评价最偏重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他说:
“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同时说部,无以上之”(8)。

《中国小说史略》
这一段引文“刻露而尽相”,堪称描写妒妇的经典。
潘金莲没有像明清小说中诸多的妒妇那样直接致人死命,而是借题发挥,以打狗、打丫头来抒发满腔妒火并折磨情敌李瓶儿及其孩子。
她对秋菊的行为则完全可以理解为性挫折引发的虐待狂行为。
这样的描写因为没有情节的起落,很容易被当作“老婆舌头”而忽略,事实上,正是“妙文”所在(9)。
诸如此类的琐碎描写在书中随处可见。
张竹坡《读法》之三十七说,《金瓶梅》“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其人生日,某人某日请酒,某月某日某某人,某日是某令节,齐齐整整挨去”;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说,《金瓶梅》“摹写人物事故”,“米盐琐屑”能使“画工化工,合为一手”;
的确如此,《金瓶梅》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充分运用了说唱艺术长期发展起来的细节描写手法”,“对饮酒、吃饭、穿衣、住房等细节都作了具体的描写,例如每一次宴会的菜谱,都不厌其烦地作了详细记录。”(10)
在大量的琐碎细节中,只有一部分与推动情节有关,更多情况下,是为了体现人物性格或构造作品的整体氛围。
夏志清先生说,《金瓶梅》“那种耐心描写一个中国家庭中卑俗而且肮脏的日常琐事,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在以后中国小说的发展中也鲜有任何作品能与之比拟。”(11)
邓之诚《骨董琐记》引《茶余客话》语:“后来惟《醒世姻缘》得其笔意”,大概是就汪洋恣肆的细节描写而言。
我们认为,在后来的家庭小说中,撇开“卑俗肮脏”不说,仅就描写“日常琐事”来说,《红楼梦》可谓“深得《金瓶》壸奥”(12);
其次《醒世姻缘传》,再次《林兰香》,都有类似的神韵。
诸联《红楼评梦》说,《红楼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漫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
应该包含了对两者琐碎笔墨的比较,一写累世簪缨的贵族之家,一写粗鄙淫滥的暴发户之家,“日常生活”自然雅俗有别。

《林兰香》
二、以一个家庭为主线,串联许多家庭的故事
张竹坡在《读法》之“八十四”中总结说:
“《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夥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
“因一人写及一县”,的确是我们理解《金瓶梅》形式和内容特点的一大关键。
石昌渝先生曾指出,《金瓶梅》完成了“长篇小说由联缀式转变为单体式,由线性结构再转变为网状结构”的文体飞跃,并解释和评价说,网状结构“是指小说情节由两对以上的矛盾的冲突过程所构成,矛盾一方的欲望和行动不仅受到矛盾另一方的阻碍,而且要受到同时交错存在的其他矛盾的制约,而冲突的结果是矛盾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料到的局面。
这种情节的横断面上贯穿着两种以上的矛盾,其轴心是主要矛盾,横断面像一张蜘蛛网,其他次要矛盾点都归向轴心,也牵制着轴心。这种结构切近生活的实际情形,是小说结构的高级形态。”(13)
以“网状结构”来描述《金瓶梅》文体结构上的特点和成就已得到学界的公认,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网状结构这一形式特征与作品的内容密切相关,具体来说,《金瓶梅》中西门一家的兴衰是主要矛盾,是轴心;
与西门一家相关的其他众多家庭故事构成错综复杂的“横断面”。
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可以将《金瓶梅》的这一特点通俗地表述为:以一个家庭为主线,串联许多家庭故事。
当然,“横断面”上的“网眼”不止是家庭故事,还有其他社会活动和场景。
《金瓶梅》“以一家写多家”的作法对此后家庭小说尤其是长篇家庭小说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模式意义,乃至成为这一类作品的常格。
如:《醒世姻缘传》前二十二回以晁家为主线,后七十八回以晁源后世狄希陈所在的狄家为主线,串联了计氏一家、晁氏族人许多家、薛教授一家、连春元一家、汪为露一家、单于民一家、童寄姐一家、陈六吉一家、郭总兵一家等等;
《林兰香》以耿家为主线,串联了燕梦卿娘家、林云屏娘家、宣爱娘娘家、任香儿娘家、平彩云娘家等;
《红楼梦》以贾府为主线,串联了史、王、薛三大家族,还穿插了甄士隐一家、林如海一家、刘姥姥一家以及众多贾府族人、仆人的家庭故事;
《歧路灯》以谭家为主线,串联了孔耘轩一家、王春宇一家、娄潜斋一家、盛希乔一家、惠养民一家、巫翠姐娘家、张类村一家、谭绍衣一家等;
与这些作品相比,被众多论者当作“艳情小说”的《姑妄言》牵涉到的家庭最多,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认为从描写家庭生活这一角度来看,它也可以说是“家庭小说”,对此,我们在后文将有专门论述。
除了这些公认的具代表性意义的家庭小说之外,其他如《炎凉岸》、《雅观楼》、《金石缘》、《幻中游》等小说也都叙述了至少两家以上的故事。

三、关注家庭/家族的整体命运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
“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襦,何美丽也;鬓云斜軃,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弄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
这里,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概述了西门氏的繁华和豪奢,最后点明“乐极悲生”的必然性规律。
这一段话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金瓶梅》的创作思想,并在无意中确定了家庭兴衰题材作品结构的基本模式(14)。
张竹坡更是直截地说,《金瓶梅》是“一部炎凉书”(第30回评),“总是冷热二字,而厌说韶华,无奈穷愁”(第7回评)。
作者依次描写西门庆谋娶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财色两得;
又放官吏债,并结交权奸蔡京,由破落户一跃而为“居五品大夫之职”的“金吾卫副千户”,至第三十回,“生子加官”,可谓“热极”,可是,“未几而冰山颓矣,未几而阀阅朽矣”(15)。
不过一年零两个月之后,官哥儿夭折,随即李瓶儿气病而终;
李瓶儿母子死后不到半年,西门庆纵欲身亡。
“西门庆临死之时,有喊叫的,有逃走的,有诈骗的,不啻灯吹火灭”(16)。
西门庆既死之后,李娇儿盗财归院之后别嫁;
潘金莲和春梅因与陈经济乱伦而被赶出家门,一横武松死刀下,一做了统制夫人之后纵欲丧命;孟玉楼带着当初的“嫁妆”再次“爱嫁”;
孙雪娥与来旺私奔之后沦落为娼;
西门大姐不堪陈经济凌虐自缢身亡;
伙计韩道国、汤来保拐财欺主;应伯爵反面伤情;
吴典恩恩将仇报;
只剩下吴月娘和她的“墓生儿子”孝哥儿凄凉度日,最后孝哥儿又被和尚化去,这样,书中“有名人物,花开豆爆出来的,复一一烟消火灭了去”(17),可谓“凉极”。
全书一百回,西门庆死于第七十九回,如果真如张竹坡所说,“此书独罪财色”(18),那么写到西门庆之死足矣,可是作者却以五分之一强的篇幅描写了西门一家的衰败景象,这在作者,或许只是为证“果报”,可是,客观上却的确写出了西门氏由“聚”而“散”、由“热”而“凉”的全过程,写出了“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19),“春梅游玩旧家池馆”一段则已成为同类小说中描写家庭衰败的经典意象。

《金瓶梅》连环画
《金瓶梅》对家庭整体命运的关注以及由兴而衰的形式和内容都具有典范的意义,家庭或家族的兴衰几乎成为后世长篇家庭小说固定不变的内容和情节双重模式,巴金、茅盾、张爱玲等人的家庭小说亦不例外。
就明清几部主要家庭小说来说,最典型的是《林兰香》和《红楼梦》。
《林兰香》中耿家是明代开国功勋之后,世袭国公爵位,作品主要写主人公耿朗与六位妻妾因缘遇合又风流云散的经过。
结尾的时候,耿朗及六位妻妾相继离世,他们的遗物集中收藏在一座小楼,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耿家的繁华旧事成为弹词、戏文的题材供人传唱。
作品表达的是“人且不能长享其春秋,物又何能恒留于宇宙”(第64回)的梦幻意识,充满浓厚的悲剧色彩。
《红楼梦》更是生命之美、尘世人生、贵族家庭的三重挽歌(20),纵算是“兰桂齐芳”,也遮不住盛筵已散、繁华过后的凄凉。

《红楼梦》
相比之下,《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的情况要特殊一点。
《醒世姻缘传》中的晁家在“女中丈夫”晁夫人的苦心经营之下衰而复兴,在她去世之后,子媳分别住进庵庐,成为苦行焚修的善男信女;
狄家凶悍的薛素姐病死,狄希陈与童寄姐平淡度日,晁狄两家的命运似乎都无太大的起落。
可是,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就会发现,全书的故事都是在由盛而衰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是透过秩序混乱的小家庭写大社会的盛衰。
在第二十三回中,叙述者对明初的民风世俗充满了赞叹和怀恋,篇首诗说:
“去国初淳庞未远,沐先皇陶淑綦深,人以孝弟忠信是敦,家惟礼义廉耻为尚。贵而不骄,入里门必式;富而好礼,以法度是遵。食非先荐而不尝,财未输公而不用。妇女惕三从之制,丈夫操百行之源。家有三世不分之产,交多一心相照之朋。情恰而成婚姻,道遵而为师弟。党庠家塾,书韵作于朝昏;火耨水耕,农力彻于寒燠。民怀常业,士守恒心。宾朋过从而饮食不流,鬼神祷礼而牲牷必洁。不御鲜华之服,疏布为常裳;不入僭制之居,剪茆为屋。大有不止于小康,雍变几臻于至道。”
这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通俗化表述,也是作者想象和虚构的明初社会“盛”景,与作品所描写的尊卑颠倒、道德沦丧的晚明现实构成鲜明对比,对此,我们将在有关《醒世姻缘传》的章节中作进一步的阐述。
《歧路灯》表面是写谭家由盛而衰由衰复兴的经历,深入一层看,主人公谭绍闻在内外合力的推动下改邪归正或然可信,谭家的“复兴”却显得勉强。
有论者认为,“小说最后安上的那条光明的尾巴——谭绍闻父子先后中魁,俱受皇恩,光宗耀祖,家业复初,不仅严重削弱了作品前本部分的批判力量,而且为垂死的封建社会唱了一曲衷情的颂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和削减了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21)。
而事实上,作者对谭家的“复兴”处理是低调而有现实依据的。
谭绍闻父子一个中了举人副榜,一个中了进士,叙述者却特意点明:“未得高官厚禄”(第108回);
谭家赎产的银钱来自忠仆偶然掘得的窖藏;
在篑初的婚礼上特意点明其嫡母巫氏是个不晓事理的“村姑”,在“兴衰”主题之下,这些细节都有了深一层的寓意。
联系书中堕落的官宦子弟盛希乔、张绳祖、夏逢若等人的故事来看,作者对谭家的未来依然持保留和担忧的态度。
比起明清小说戏曲中那些动辄“状元及第”、“安享荣华”的大团圆结局来说,《歧路灯》的结尾算不上太“光明”,也难说是“颂歌”。
李绿园本人早年(30岁,1736年)曾中举人,晚年又有过近二十年的仕途生涯,做过贵州印江知县,在他辞官返乡之后的第二年(69岁,1775年)次子中进士。
《歧路灯》的后半部分即写于晚年辞官返乡之后(22),因此,作者父子的经历可以为谭氏父子“中魁”的情节做注脚,这并没有违背他“严格而固执的写实态度”(23)。

《歧路灯》
中国古代士子以科举出仕为人生理想,像《红楼梦》中的贾府和《歧路灯》中的谭家这样的门第,就算败落了或曾经败落过,子孙中出一两个科举人物完全在情理之中。
就事论事,我们并不认为“兰桂齐芳”和“父子中魁”的结尾就一定有损“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就李绿园来说,他对家庭的兴衰始终有着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在《歧路灯》第三回,谭家方兴未艾,叙述者就通过两位正人君子之口对家庭的兴败表现出了焦虑、困惑和无奈,谭孝移和好友娄潜斋从子弟教育问题谈到“兴败之故”:
孝移把王氏胡缠的话,笑述一遍。
潜斋也大笑说道:“……自古云:教子之法,莫叫离父;教女之法,莫叫离母。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那资性鲁钝的,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那资性聪明些的,将来出了书屋,丢了书本,把平日理学话头放在东洋大海。我这话虽似说得少偏,只是教幼学之法,慢不得,急不得,松不得,紧不得,一言以蔽之曰难而已。”
孝移道:“兄在北门僻巷里住。我在这大街里住,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
潜斋道:“人为儿孙远虑,怕的不错。但这兴败之故,上关祖宗之培植,下关子孙之福泽,实有非人力所能者,不过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已。”
同样完成于乾隆丁酉的《家训谆言八十一条》可以与《歧路灯》中这一类内容互相参证(24)。
回到我们的中心话题,《歧路灯》详细描写了谭家的败落,结尾虽然有“复兴”的迹象,并不影响“家庭兴衰”的主题。
值得指出的是,在“家庭兴衰”的话题之下,由于作者的思想境界、身世遭遇、审美旨趣等不同,不同作品具体关注的焦点也不相同。
《金瓶梅》主要关注情色对个人及家庭的摧毁;
《醒世姻缘传》主要关注的是夫妇以及其他家庭伦理的颠倒;
《林兰香》虽然也关注多妻制家庭中的夫妇关系以及贵族子弟的教育,但是,对家族衰败命运的解释却接近道家的“循环”之说,当象征耿家繁华旧事的小楼焚毁之后,燕梦卿托梦给她的儿子:“理数如斯,于汝何罪”(第64回);
《歧路灯》主要关注子弟教育;
《红楼梦》的内涵最为丰富深厚,它几乎囊括了前述各项主题和内容,这也是它凌驾于所有同类作品之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顺便提及,不少论者在讨论时称“西门家族”(25),似乎不太妥当。
如“导论”中所说,家庭和家族是有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两个概念,家庭是个体,是基础;家族是多个家庭组成的群体,是上一级组织。
一般情况下,家庭是同居、共财、合爨的单位,而家族是别籍、异财、各爨的群体,二者区别比较明显,只有当一个大家庭发展到几百甚至数千人口,聚居于同一村落而又没有分财别籍时,家庭与家族才合而为一。
因此,《金瓶梅》描写的只是西门庆“家庭”的故事,《红楼梦》描写的才是贾氏“家族”的故事。

《醒世姻缘传》
四、建构“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内在意义模式
《金瓶梅》以“家庭”为中心,辐射到社会诸多方面,甚至直接与朝廷关联,构成了“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内在意义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常常把家庭作为国家的基本或者说微型结构,《论语》说:“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都强调父与君、家与国的必然联系,“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处于“家”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即是一般所说的“社会”,包括社区和各级官僚机构。
在儒家规定的文化秩序里,个人的道德规范和国家的政治行为先验地、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大学》对此作了经典的表述: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6)
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孔子《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都是强调修身与治国、孝弟与忠君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而家庭伦理、社会约法和国家管理的基础都是道德层面的“礼”。
孟德斯鸠对中国古代的“礼”有着浅俗而精彩的论述:
“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还要父亲以仁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27)。
这种小家和大家在深层结构上的统一导致了伦理和政治的混同。
在中国古代的世情小说尤其是家庭题材小说中,家国同构、伦理和政治混同的文化特点得到非常形象的表现。

孟子像
在早期短篇白话小说中,也有对家庭生活的描写,而且由家庭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社会,但是关注的多是个人的命运和际遇,很少与国家关联。
最早明确地以“家”喻“国”、将家庭与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金瓶梅》。
美国学者凯瑟琳•卡尔丽茨《〈金瓶梅〉以家喻国的影射》一文对《金瓶梅》中“家国关系”的“诠释”也许有“过度”的嫌疑,但的确颇具启发意义,她认为,“西门庆是明王朝的一个缩影”,《金瓶梅》将隐含着的批评矛头直接对准了北宋徽宗王朝(28)。
西门庆家中的六房妻妾是否“象征着地方上的六部”,值得商榷;说“《金瓶梅》将整个万历事件通过小说形式烙印在读者心里”更是冒险的推论,因为根据新近的研究成果,《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已被框定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八年左右之间(29),万历八年,万历皇帝还只有十七岁,他对郑妃的宠幸到十八岁才开始,郑妃生子以及立储之争更是多年之后的事情。
不过,西门庆和妻妾们的关系的确与皇帝和后宫嫔妃们的关系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而且,作品中所引用的部分歌曲内容是歌颂皇帝的,似乎是用来将西门庆与皇帝做比较(30);
潘金莲曾公开抱怨说,李瓶儿“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第31回);
官哥儿的满月宴席上有两位内官到场,在讨论曲目时,薛太监还说:“俺每内官的营生,只晓的答应万岁爷”,诸如此类的细节,似乎在不断提醒读者,西门府就是一个微型的朝廷。
西门庆重金贿赂蔡京,得副千户之职,任本地提刑所理刑,掌管刑狱,从市井棍徒摇身变为从五品官员,后来还转了正千户掌刑。
叙述者就此事公开进行议论: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
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
夤缘钻刺者,聚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
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繁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第30回)
这里,将矛头直接指向徽宗;第七十一回也直写徽宗:“朝欢暮乐,依稀是剑阁孟商王。贪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而“朝欢暮乐”、“贪色贪杯”也正是西门庆的写照。
作品结尾,在逐一交代西门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家庭“解体”的同时,又特意写到了北宋朝廷的倾覆。
西门庆失德,致使家庭生活秽乱不堪而终于“家亡”;
宋徽宗失德,致使天下风俗颓败而终于“国破”,这样,家庭与帝国、小家长和大家长、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在内在语义上表现出了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
小说写的是宋徽宗时期的“历史”,却时时让读者联想到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现实”。
西门庆上任之后,公开贪赃枉法。在他还是“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的西门大郎和西门大官人时,他整日与一班市井棍徒鬼混,并依靠财势与周守备、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等地方官吏攀交情;
成为正式的官僚之后,即利用一切机会与蔡太师、蔡状元、宋巡按、蔡九知府等上层官员周旋,并讨好内官,以换取更大的利益。

宋徽宗像
从西门庆辐射开来,作品写到了广泛的社区生活和官僚机构的运转情况,从而对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金瓶梅》之所以被一些论者称为社会小说,主要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的内容。
关于《金瓶梅》在暴露社会黑暗方面的现实主义成就,早已有不少很有深度和力度的研究成果,如徐朔方先生《〈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黄霖先生《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章培恒先生的《论〈金瓶梅词话〉》和孙逊先生的《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等等,这里不赘。
《金瓶梅》从一个家庭辐射开来写广阔的社会,并通过“明写”和“暗喻”两种方法将笔触伸向朝廷乃至皇帝本人,从而将家庭、社会、国家三者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内在意义模式。
这一点对后世家庭小说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这一模式中,家庭只是一个相对的起点,进,可以向社会乃至国家开拓;退,则可以向家庭成员的个人生活乃至内心开拓。
在明清世情小说中,家庭小说的成就和地位最为显赫,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三位一体”的模式不仅可以提供自由驰骋的艺术想象空间,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家国同构、伦理道德与政治法规不分的本质特征,从而在艺术和思想两个方面都为创作者和阐释者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
在明清家庭小说中,从家庭到社会这一层次的开拓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只有《醋葫芦》、《痴人福》等少数几部作品的故事比较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其他绝大多数都延伸到了“社会”。
至于与“国家”的关系则比较复杂,有的像《金瓶梅》一样直接写到朝政、宫廷或皇帝本人,如《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炎凉岸》、《姑妄言》等;
有的从隐喻的层面以小家庭影射整个大世界,如《醒世姻缘传》等;
有的则止于“社会”,基本上与“国家”无涉,如《疗妒缘》、《清风闸》、《雅观楼》等。
综上所述,我们从四个方面概括论述了《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
即:以琐碎的笔墨描写日常生活;
以一个家庭为主线,串联许多家庭的故事;
关注家庭/家族的整体命运;
以“家庭”为中心,辐射到社会诸多方面,甚至直接与朝廷关联,构成“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内在意义模式。
这不仅是对《金瓶梅》作为家庭小说的特征的总结性研究,也为此后家庭小说的辨别和定位提供了参照性标准。
在比较中可以发现,《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红楼梦》等几部长篇家庭小说基本上都符合《金瓶梅》模式,其他则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些作品的实际成就似乎已经证明,《金瓶梅》所提供的是家庭小说最完善的模式。

《金瓶梅词话》
注:
1、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之九十七、之百三,见侯忠义等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印。
2、 第一回崇祯本眉批,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3、 刘廷玑《在园杂志》,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4、 张竹坡《第一奇书凡例》,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5、 张竹坡《读法》之三十七,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6、 夏志清《古典小说史论》第20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 杨沂《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收入《金瓶梅西方论 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44、142页,东方出版社,1996。
9、 张竹坡《读法》之七十一,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10、程毅中《〈金瓶梅〉与话本》,原刊《金瓶梅研究》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1;收入盛源等选编《名家解读金瓶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1、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171页。
12、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十三回眉批。
13、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364页,三联书店,1995年2印。
14、朱萍《悲凉之雾 遍被华林——明清家庭兴衰题材章回小说的文化意蕴》, 《学术研究》,2000年第8期。
15、《竹坡闲话》,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16、《满文译本金瓶梅序》,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17、《读法》之二十六,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18、《竹坡闲话》,见《金瓶梅资料汇编》。
19、孙逊《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原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 版),1980(3),收入《名家解读金瓶梅》。
20、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第六章,学林出版社,1997年3印。
21、肖星明《〈歧路灯〉现实主义局限性原因初探》,《广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7(1)。
22、《歧路灯自序》署“乾隆丁酉八月白露之节”,其中说:“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即:李绿园于乾隆甲午(1774)返乡之后开始续写《歧路灯》,乾隆丁酉(1777)年完成。
23、栾星《李绿园传》,见栾星编著《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
24、李绿园《家训谆言八十一条》,见栾星编著《歧路灯研究资料》。
25、如田秉锷《统治思想趋于崩溃及旧伦理的沦丧——〈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及社会意义》:“《金瓶梅》的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个家族的发迹与瓦解。西门家族的瓦解,不是开始于西门庆的自然死亡;远在这一家之主活蹦乱跳的时候,瓦解的条件便已酝酿成熟。”见王利器主编《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91页,成都出版社,1991;及巨涛《论〈金瓶梅〉中的西门氏家族社会》:“综观中国古典小说,有两个令人瞩目的家族社会模式:先是《金瓶梅》中西门氏家族社会,后有《红楼梦》中的贾氏家族社会。”见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第138页,齐鲁书社,1988。
26、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第895页,中华书局,2001。
27、孟德斯鸠著,张念深译《论法的精神》第312-313页,商务印书馆,1987。
28、凯瑟琳•卡尔丽茨《〈金瓶梅〉以家喻国的影射》,见《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
29、陈大康《明代文学史》第443-44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30、(美)柯丽德《〈金瓶梅词话〉中歌曲的三大隐喻》,见《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节选自《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1、问:段江丽:《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什么时候上映时间?
答:这部影片的上映时间是2024-04-20 03:13:34
2、问:段江丽:《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国产剧在哪个电视台播出?
答:段江丽:《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目前只有华数TV、1905电影网、咪咕视频、河塘影视等线上播出,而且还没有在电视上播出。
3、问:国产剧段江丽:《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演员表
答:在线观看非常完美是由达达执导,凯瑟琳·海格尔,萨拉·乔克,耶尔·雅曼领衔主演的国产剧。
4、问:哪个平台可以免费看段江丽:《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
答:免vip在线观看地址http://www.vk126.com/jianzhan.asp?id=170
5、问:手机版免费在线点播有哪些网站?
答:hao123影视、百度视频、锦祥剧情百科网、PPTV、电影天堂
6、问:在线观看非常完美评价怎么样?
Mtime时光网网友评价:2023热播《段江丽:《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楚岩笑了笑,也不否认,继续道可前辈有没有想过,这一次结束后,上古前辈突破十二界,实力又提升了一大层,那此地的压力,必然也会增长,没有新的力量进入,这压力可就要前辈们自己承受了。
丢豆网网友评论:王勇强行挤出点笑容来,期盼着江虎能接受他的提议。结果江虎给了他一窝脚,冷笑道:你当老子是傻子吗刚刚老子可是亲眼看到有鬼手从宅子里伸出来,明显有鬼,这地方谁还敢要,谁敢住还两亿,二块钱老子也不要
游客bx5NOD3网友评论:2023热播 《段江丽:《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庭小说模式》等到第六层的时候,在这里终于感受不一样的气息,一团团属于地狱之塔的力量,在和那股奇异的力量相互僵持着,而在这个中间的地方,一个通天的白色石柱耸立在那里,在他的四周无数涟漪不断翻腾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