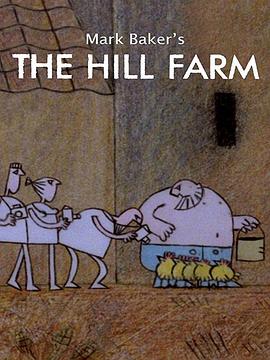- 1.NBA 76人vs尼克斯20240423已完结
- 2.007之霹雳弹[电影解说]已完结
- 3.NBA 马刺vs森林狼20240228已完结
- 4.德甲 弗赖堡vs法兰克福20240218已完结
- 5.86 -不存在的战区- 第二季 86―エイティシックス― 第2クール12集全
- 6.青梅竹马绝对不会输的恋爱喜剧全集
- 7.疯狂希莉娅HD
- 8.孤独的美食家 第二季已完结
- 9.再见妈咪1986HD
- 10.喜气逼人HD
- 11.失魂客栈HD
- 12.陶宝萍的幸福生活HD
- 13.大人物2011HD
- 14.脂粉市场1933HD
- 15.理查三世:看不见的故事已完结
- 16.亲朋密友已完结
- 17.永生之战HD
- 18.恐龙飞车HD
- 19.神奇的费曼先生HD
- 20.欢迎光临千岁酱已完结
今年上半年,热播剧《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开播。一面世就引发了一轮收视、讨论热潮。围绕该剧的思考,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人工智能有关的。
比如,这些最常见的:人工智能拥有了意识怎么办?人工智能会不会密谋反攻人类?和人工智能谈恋爱会有哪些问题?我们能不能和人工智能融为一体?古今中外的科幻故事,可谓把这些话题都聊了个遍。
《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2022)剧照。
在作家陈楸帆看来,我们需要跳脱一种二元论的模式:要么怕这个机器,要么崇拜它或者当它的主人。而是要想象更多可能。从这点上来看,人类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这也是《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整体的一个基调: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爱”和“死”还是宇宙间普遍的法则,在这些最原始的力量的层面,人也只是诸多生命形态的一种,当我们希望把自己关于人类的想象投射到机器、星球上时,常常是会遭遇不解的。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化脚步越来越接近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图景,科幻还能如何想象机器,以及我们与机器的关系?借新书出版的契机,我们对陈楸帆进行了一次专访。
最近,AI(人工智能)的世界似乎并不太平。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谷歌的一名叫布莱克·莱莫因(Blake Lemoine)的工程师表示自己的人工智能LaMDA拥有了自我意识。莱莫因表示,LaMDA不仅能和自己进行简单的对话,还能聊《悲惨世界》和充满禅意的故事。不过,他的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谷歌的重视,相反,他还被视作精神出了些问题。
如果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十年前,可能大家的反应会比现在轰动得多。层出不穷的描写AI的科幻小说《黑镜》《西部世界》等剧集的热播,无形中给人们的心理打了一针疫苗,增强了对未来科技冲击的免疫。类似LaMDA这样的情节即便真实发生,大家也不至于有多么惊慌失措。毕竟,有关机器的书写在科幻作品(小说、影视)中出现的频率实在是很高。
不过,最近几年比较受关注的有关机器人/人工智能的科幻作品还是会呈现出一些变化——比如近期特别火的剧集《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在过往的科幻作品的机器人书写中,作者们常常想要去回应一个问题:随着机器不断发展,什么是人不可被机器人替代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机器人主题科幻作品的终极哲学,也反映着一种难以被克服的“人类中心主义”。
陈楸帆,科幻作家,编剧,翻译,策展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艺术学院,曾多次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银河奖、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奖、茅盾新人奖等国内外奖项,代表作包括《荒潮》《人生算法》《AI未来进行式》等。曾在Google、百度、诺亦腾等高科技企业从业,现为传茂文化创始人。
相对地,在《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的很多剧集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比较明显的“去人类中心主义”风格:人类灭绝后,三个机器人巡游地球的各种大肆调侃;亡灵之夜后丧尸围城导致世界毁灭,却不过是宇宙中的一声“屁”;宇航员在外太空遇险,最终穿越有机-无机的生命界限,与卫星融为一体;深入虫群的人类科学家所坚守的人类尊严,在“智慧有碍进化”的生存逻辑面前被击得粉碎......
一方面,这种风格的变化映射着动荡的现实,也许疫情的肆虐、经济的衰退、政治的极化都让人对世界充满了失望乃至“嫌弃”,导演们索性在作品里喊出一声平时不敢喊的“毁灭吧,累了!”而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也预示着一种蕴含更多可能性的机器人想象。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归根结底是一种对文艺复兴精神中人之高贵性的挑战,旨在告诉我们人相对于机器并没有那么不同。
长期研究机器人科幻作品的学者程林曾在一篇论文里指出,机器人科幻中常常存在三种人-机器人关系:机器人臣服于人的主奴关系、机器人作为人认知自我之参照的镜像关系,和机器人相对于人是陌生乃至令人恐惧之物的他者关系。随着人工智能的进化脚步越来越接近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图景,科幻还能如何想象机器,以及我们与机器的关系?
不同风格的科幻作者会给出各自的答案。在这方面,作家陈楸帆最近做了一次新颖的尝试。他和知名的企业家、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合写了一本名为《AI未来进行式》的书,陈楸帆在书中写了十个不同的有关AI的故事,李开复则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为这些故事中涉及的技术细节提供科学的分析。两人试图通过这种“虚构+非虚构”的写作方式,为读者们勾勒一幅“近未来”的人-机器生存图景。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陈楸帆曾在谷歌工作过一段时间,业界的经历让他的写作具有一种“科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在维持想象的张力的同时,保持对技术细节的关注。在他的《人生算法》《荒潮》等旧作中,机器都是重要的角色。他还曾“辅助”AI写过小说,在他的作品《出神状态》中,就有一段由AI生成的内容。
除了爱在小说中写机器,陈楸帆也是《爱,死亡和机器人》这些科幻剧集的忠实粉丝。在我们近期的这次对谈中,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剧名:爱与死亡,这两个看似和机器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词汇,反而正是机器人科幻永恒的归宿。
AI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幻对技术的反思还很不够
新京报:你的经历比较丰富,读书时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去了科技公司,又转做科幻作家。此次的《AI未来进行式》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小说家+企业家”合作的尝试,你觉得这种写作和之前的科幻写作有什么不同?
陈楸帆:最早有这个写作的想法是2019年上半年,李开复老师的团队当时找到我,提出共同进行一种虚构+非虚构的写作。开复老师对于AI在未来发展的路径有很多细节了解,包括看起来天马行空的技术怎么在各个领域具体落地等。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怎么样比较好地用我的小说把这些想法背后的思考呈现出来,中间也和很多清华、北大、中科院的专家学者以及创新工场投资的科创公司负责人做了专访,了解AI在一个比较近未来(20年)的区间里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和风险。
我在Google和他共事过,也有过在科技公司从业的经验,所以在下笔的时候,我不会把故事设定得非常天马行空,比如直接写一个以通用人工智能为背景的故事。这本书里的故事更多是给大家一个AI发展的渐进式图景,而不是给大家塑造一个技术“突变”后的世界。
《AI未来进行式》,作者: 李开复/ 陈楸帆,版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5月
AI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在教育、娱乐、医疗等各个行业其实都已经有应用,我在具体的写作阶段,会思考如何在一个故事里把不同的技术应用场景“打包”在一起。不过这样也让一些读者觉得,这书读起来有些“命题作文”或者“半命题作文”的风格。每一章都还是会有一些相对集中要去阐释的技术点。这当然对科幻写作来说会是一种限制,但我发现这种限制其实也提升了我对写作的把控力,我会尝试调用不同文化背景里的思想资源、历史上的各种符号象征,尽可能地与我要在每一章里讨论的明确的技术形成互文,在这个单一命题的纵深中形成一种多义性。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尝试。
科幻作家有不同的风格,我一直说,我自己比较偏“科幻现实主义”,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考虑它覆盖地域的广泛性。除了我们熟知的科技大国,书里的很多章节都是以非洲、东南亚国家为背景的。中国、美国这类大国,肯定已经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快车道上了,相对来说也拥有更完备的技术和制度环境来适应这种未来,但对于很多国家来说,AI会带来更不确定的未来。提前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科幻作者应该做的。
新京报:说到这种“科幻现实主义”,这其实涉及对科幻这种文学类型的理解。有些人偏好对技术细节有严谨追求的科幻文学,也有些人会对科幻采用一种宽泛的定义,更在意“幻”的部分。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楸帆: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作的风格,我在科技公司有过从业经验,就会自然在科幻的切入点上更具象化和细节化,日常我接触的是一个产品从idea到实验室再到市场的具象过程。体现到写作的美学里,我就会更讲究“落地感”,去具体地描绘故事发生的地域环境、文化背景,而不太喜欢在一个架空的、纯虚构的背景里展开故事。围绕一个技术展开想象的时候,我也会很多地讨论执行的场景。
科幻的每种风格其实没有好坏,关键是看这个风格能否执行得精彩。莱姆的作品风格很多样,他的技术描写经常给人一种天外飞仙感,但他都能通过细致的文字把你领到背后深刻的哲学思考处。像特德·姜,有一些作品偏奇幻,比如《72个字母》,背景是一个接近于架空的世界,也有一些作品像《软件体的生命周期》,就很贴近一个未来产品经理的具体工作故事。
但他们都很清楚,讲不同风格的故事希望达到的美学效果是什么样的,再尽自己所能把这个效果呈现到极致。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特别强调“科幻文学”类别的特殊性。因为所有的文学写作其实都是去处理一个形式与思想匹配的问题:你有没有足够深刻的思想,你能不能用足够合适的形式把它准确传递出来。
《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2022)剧照。
新京报:研究科幻文学的学者宋明炜认为包括你在内的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正在引领一种新的写作风格,他称之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他认为这些新一代的中国科幻作家,都对技术发展有比较尖锐的反思。在《AI未来进行式》序言里你也有提到,和李开复撰写的专业解读对AI怀有的乐观情绪相比,你的文学写作部分更多是有批判性的。你会觉得科幻文学应该在一个科学“狂飙突进”的年代更多扮演一个批判者的角色吗?
陈楸帆:相较于身处科技浪潮中的科学家,作为科幻作者,在审视科学的时候确实大概率会站在一个批判、反思的视角上。相对来说,现在中国的科幻小说家相较于更早些时候比如上世纪80年代,这种倾向会更明显。像《小灵通漫游未来》那种代表一个时代科幻写作的作品,书写的就是一种乐观的、玫瑰色的未来。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始用文学写作反思科技,但这种反思还是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归根结底,我们的整个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话语更多是舶来品。西方世界有类似基督教、法兰克福学派这些非常悠久的警惕技术的传统,在中国,这样的传统一直是比较缺乏的。直到现在,互联网大规模嵌入日常生活,大数据、元宇宙、人工智能看起来都像触手可及的未来,大家才逐渐开始去思考我们从里面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最近像“困在系统里”的人这类话语也开始在公共空间里活跃起来,相关的反思也变得更加值得重视。
作为写作者,我们更需要站在独立的位置上,不一定要去刻意地批判资本、平台,而是要尽可能地把我们观察到的那些鲜活的人在一个结构性变动里的体验,用自己的方式反映出来。通过作品连接读者,这样的反思能积少成多,形成一种与技术浪潮相制衡的力量。
科幻要帮助人们探索更多元的人机关系
新京报:本书的故事中,AI大多给人类创造了很多便利——但熟悉此类科幻的读者们都会知道,这只是转折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作家们经常笔锋一转,讲到这些便利背后的代价。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不同文化中的作家,会在作品中呈现风格迥异的机器人想象。我们熟知的这种对机器的警惕,则更多出现在欧美基督教国家中。像亚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日本,他们对人工智能或者说类人智能的想象总体会更积极一些(阿童木、奥特曼等)。你会怎么看这些观点?
陈楸帆:的确有这个现象,中国古代其实就有所谓“偃师造人”的传说,不光是中国,儒家传统波及的东亚文明圈,对待一个机械化的他者都不会是一种对立的态度,不会把他当做“异己”来对待。我们更倾向于用“关系”来定位机器人,也会更倾向于把它们当作“类人”的存在。比如,如果中国人家里有了个AI,我们会很自然地考虑把它纳入家的框架里,考虑它在家庭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视作一种工具。日本尤其痴迷于把机器人当作人,他们很执着地创造各类人形的机器,也是“恐怖谷”这类理论诞生的地方。
不仅如此,日本人也非常关注一个类人、但又不完全是人的存在对人心灵的冲击。此前北大的博古睿研究中心出过一本书(《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就是从儒释道哲学的角度来反观AI,这些中国传统的思想其实都强调人和人工智能之间建立跨主体间性交流的重要性。这些思想未来可能会变得更重要。我想现在写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小说需要做的就是探讨尽可能多元的人机关系,我们需要跳脱一种二元论的模式:你要么怕这个机器,要么崇拜它或者当它的主人。这种模式其实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就已经奠定了,过了接近一百年,我们应该有更多想象的突破。
《大都会》(1927)电影剧照。
新京报:你觉得这些可能性还有哪些?
陈楸帆:有一些比较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方向。比如人工智能的意识和人的意识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人和机器的差异。前一阵子谷歌的工程师Lemoine宣称AI觉醒引发争议,反映的就是有关意识的问题。科幻小说对意识问题的探讨未来会显得特别关键,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真正跨越不同意识种类去实现主体之间的交流。
新京报:在《双雀》里,你其实也讲了一个人和AI合作成长的故事。我记得你自己也和人工智能合写过一篇科幻的作品,这可以说也是你自己进行的一种与AI关系的探索,你有什么体验?对于科幻小说作者来说,能和从AI的互动中获得哪些帮助?
陈楸帆:我和AI合作的写作不止一次,同时它的算法也不断在升级,2020年我们用了GPT-2(通用预训练转换器),用了更强大的算力和数据来训练模型,现在有了更强大的GPT-3,它的写作能力会更强。和它合作写作的时候你会明显意识到也许机器比你更了解自己,它能把你写作过程中无意识的结构提炼、显现出来,让你看到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某种写作套路或是语言使用习惯。
但另一方面,它的写作本质上是带有随机性的,它生成的文本有时候也会不按套路出牌,打破你常规写作的一些思路。这也倒逼作家去适应它的思路,把它的创作变得前后自洽。有时候“细思极恐”的是,看起来是你在用写作训练它,但它也在无形中通过你的训练交互训练着你。
新京报:感觉这像是一个套娃式的结构,我想起你在书里写的一篇《双雀》,两个小男孩就是和AI一同成长。这本来是你笔下的主题,现在仿佛是你把自己变成你小说里的这个角色一样。
陈楸帆:其实我们都早已生活在一种套娃式的结构里了,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数字工具来量化自己的生活:计算自己的运动量、消耗的卡路里等等,再根据工具的反馈来调整自身生活的习惯,反过来这些习惯的改变又会被机器学习。本质上这种套娃就是一个控制论的思维模式,以后这种“计算-反馈”的机制会更深地嵌入到我们的意识、语言中。
《西部世界》第一季(2019)剧照。
新京报:莱姆也是写机器人科幻的高手,有学者考证,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反思机器人科幻的笔记,其中他就提到,他那个年代以机器人为主题的科幻小说经常忽略有关“宗教”的问题,而宗教问题对于认识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到了今天,我们会发现机器人经常和宗教在科幻中“联姻”。《西部世界》《爱,死亡和机器人》这些科幻剧集,包括你这本书里的《一叶知命》等都是如此。我个人会认为,机器与宗教的碰撞,是两个与人类相对的“终极他者”的碰撞,就很容易制造出吸引人的想法和情节上的张力。你又会怎么看宗教与机器的关系?
陈楸帆: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强调“唯物”的社会里,但我们也知道,像宗教史和科学史、科学技术发展与所谓的魔法、玄学的历史,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甚至所谓的玄学助推了科学的发展。在科幻里,我们可以暂时放弃宗教和科学的二元对立,它们都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各自有边界,有其解释范围之外、力所不能及之处。但就其关怀来说,科学和宗教其实都希望追问那些对于人类来说最终极的问题。在这方面,科幻恰好游走在灰色地带里,能够同时嫁接两者对于终极问题的关怀,具体就可以体现到你说的,机器人故事和宗教文化经常同时出现。
有时候人们面对宗教产生的那种敬畏感,和面对机器人时的感受很像。当我们创造出令我们自己都惊叹的技术,AI也好、元宇宙也好,我们也会对自己的造物产生一种类似面对宗教时的敬畏与惊奇,并随之产生一种顿悟式的警惕。
新京报:你在《职业救星》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构想:传统工人们被人工智能取代后进行职业再造时,其中的一家公司给他们提供的方案是让他们“玩游戏”,他们通过在虚拟世界中帮助其他地区的工地盖房子来“自我实现”,但其实这些工地也是虚拟的。我前几天在读哲学家伯纳德·舒兹的名作《蚱蜢》,他有一个很颠覆常识的观点: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运行的本质,其实就是游戏,未来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人类真正的意义归宿也在游戏中。你会怎么看这个观点?
陈楸帆:这本书大部分的故事其实都和游戏化有关,我写很多故事也都喜欢采用一个游戏化的结构,可能因为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游戏玩家。我一直觉得游戏是人性最基础的一个需求,这种需求远远比现代社会人对工作意义建构的需求要基础。就像《游戏的人》里说的,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人类文明,我们大部分的社会活动都在模仿游戏的结构。我们也经常喜欢用一个隐喻来比喻人生:人生就像一场游戏。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技术的发展让我们也到了这么一个节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游戏的价值。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游戏在传统文化里经常是被贬低的,在现实层面相关的产业也都会遭遇一些限制。但它确实不仅仅应该被当作一种打发时间的纯粹娱乐,而是可以去建构起人的基础意义,乃至未来能帮助人与人之间形成公共联结。这种联结可以是跨地域的,还可以是跨世代的。除此之外,我们生存的环境越来越不确定,游戏是一种面对高度不确定世界时人大概率会选择的应对策略。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它也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大众文化隐喻,“头号玩家”“失控玩家”,“玩家”成了新一代的身份认同。
很多人可能担心的是,如果游戏对于人建构意义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它又是发生在虚拟世界中的,总归不是很好。这里我觉得是一个认知范式转换的问题。我们可能要在一个虚实混融的年代重新理解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拟”,而不是始终被困在一种物质主义的迷思里面。我们在虚拟世界里得到的归属感、满足感、自我实现感,在技术发展的某个阶段,未必不能是真实的。
《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2022)剧照。
人相对于AI不可替代之物,为什么永远是“爱”?
新京报:我觉得《爱、死亡和机器人》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特点:它无意中点出了死亡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前段时间《南方周末》写了篇报道,讲了一个算法工程师试图通过AI“复活”已经过世的外公的故事。这类故事原型也出现在《黑镜》中。如果我们考古一些前现代的机器人历史,像在中世纪的时候,机器人想象确实是和巫术、魔法相联系的。和机器对话,和与“亡灵”对话,某种程度上也很相似,都会产生一种接触完全不可知的他者时的冲击。我不知道这种联系是否是偶然的?你会怎么看待死亡和机器这个主题?
陈楸帆:我在《偶像之死》的开篇里其实也写了一个类似的场景,粉丝们通过巫术与偶像的虚拟化身“神会”。就像你说的,AI和“灵媒”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人做很多事情的心理需求结构是不变的,不管我们是希望用AI、算法,还是用所谓的巫术去试图和故去的亲人重新建立沟通,都蕴含着相似的沟通生死的冲动。
我也很喜欢“爱,死亡和机器人”这个名字,我们知道爱欲和死的欲望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里是人类最为根本的两种原始的驱力,当它们和机器人并置,其实我们就已经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虽是人类的造物,但依然和人一样是处于爱-死驱力之间挣扎的存在,它是一种有别于纯粹工具的、独特的意识主体。从这点上来看,人类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这也是《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整体的一个基调:非常地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像《虫群》《恰是机器脉冲的颤跳》《僵尸之夜》这些剧集都是在反映这个问题。到最后,“爱”和“死”还是宇宙间普遍的法则,在这些最原始的力量的层面,人也只是诸多生命形态的一种,当我们希望把自己关于人类的想象投射到机器、星球上时,常常是会遭遇不解的。
《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2022)剧照。
新京报:这种爱与死之间的张力也在收官剧集《吉巴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被各家媒体和观众们讨论的最多的一集。
陈楸帆: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集,导演创造了一个很奇妙的文本,能用一个场景传递出如此多义性的内容,这里面的隐喻太丰富了,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关于这些层面的分析文章都已经很多了,我个人最欣赏的一点是这集对爱与死张力的展现:女妖所代表的爱欲与原始的、自然的生命力,和骑士所代表的理性化人类文明之间的冲撞。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张力的呈现有很强的具身性,身体感官(比如听觉)在这场冲突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人会忽视的一点是,身体是人和机器之间区分很重要的一个边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身体,而身体获得的经验并非完全都是机器接收到的那种“数据”。这几十年,具身认知理论的发展让我们意识到大量的认知过程并不仅在大脑皮层产生,而是发生在身体的各个部位。皮肤乃至内脏,都是我们认知世界的重要媒介,我们是用整个身体在和世界打交道。如前所述,我们现在很关注机器能否模拟人的意识的问题,但在意识之外,人拥有的这具独特的身体中发生的很多下意识反应、潜意识的认知过程,机器是否可以模拟?这可能是更大的未知数。西方文化中的那种身心二元论长期会贬低身体的地位,我想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反而让我们意识到要重新重视起我们人类的身体,乃至回到一种身心的一元论上来。
因此我也觉得,像《吉巴罗》这样的剧集,你当然可以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去“拆解”它,去阐释它的各种层次的隐喻。但作为观众,最重要的是用你的感官去接受它带给你的那种整体的冲击,那种最直观的审美体验是最重要的。与之相比,条分缕析的理论反思是一个二阶的反应。
《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2022)剧照。
新京报:如你前面提到的,“爱”与“死”是宇宙间两种根本的法则,其实它们也是影视剧最喜欢阐释的主题。与AI相关的科幻小说经常会拷问一个问题:人类究竟是否拥有AI无法取代的东西?作者们常常把这个主题落脚到“爱”。近些年,科幻作品频频给出的这一“答案”,似乎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陈词滥调。你怎么看?
陈楸帆:我记得诺兰的《星际穿越》重新上映的时候我又看了一遍,我觉得和第一次看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会对导演最后又把想讲的故事落到“爱”上感到有些没劲,像你说的,有些陈词滥调,但这次重看,我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因为这些年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我想可能在大部分人的语境里,“爱”会被单纯窄化或者降格为一种人世间的“情爱”,比如亲情、爱情或者纯粹的“情欲”,但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说,爱可以是一种“引力波”式的存在,引力波让我们的星体得以存在,如果没有了它,星体难以凝聚成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它,我们的生命、意识也无法存在,在最前沿的天体物理学里,引力波是有可能超越维度的,这其实就很像《星际穿越》讲的那个故事。所以我想这是很多科幻电影在表达爱这个主题的时候真正想说的——它是一种宇宙中基础的力量。
《星际穿越》(2014)电影剧照。
爱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物理学现象,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现象,也许不管我们这些科幻作家的故事讲得多么复杂精妙,都会被这个主题牵引回来。为什么呢?可能真的是因为除了爱之外,我们一无所有。至于说人有没有AI不可替代的东西,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个人目前能想到的就是:你借助自身的感官收获的体验。机器可能可以去模拟,但体验本身还是属于你的。
科幻写作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新京报:本季的一些剧集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现实的影响,比如《丧尸之夜》那集,就映射了疫情恐慌、特朗普当政等。在你的这本《AI未来进行式》里,也有很多章节都是在疫情的背景下发生。这让我想到之前看到的一个观点: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疫情都将极大地重塑文学想象的方式。你个人觉得疫情可能会对世界和中国的科幻写作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陈楸帆:可能不止是疫情,大的战争、政治冲突、经济萧条,都有影响。美国的两次大萧条之后,都会产生一些倡导一种避世主义的文学,那种玄妙的超自然主义流派也是在一战、二战之间兴起的,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人们要么可能会选择一种逃避现实的策略,比如享乐主义、虚无主义,要么会去寻求一些超越性的信仰,比如前面提到的信仰、玄学。其实科幻很多时候都会被当作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因为那么多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外太空,跟地球没什么关系,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没什么关系,读者的视角是可以抽离的。就像《爱,死亡和机器人》里的一些剧集讲的,可能人类的事儿就只会在宇宙里闹出一点小动静。
这次疫情也好,历史上很多次类似的灾难也好,它们给人类的情感、给文学风格带来的影响是有轮回性的。不过我们这个年代更突出的一点可能是技术越来越多地成为文学中重要的隐喻。不管是机器人,还是算法、大数据之类,我们不管讨论什么样的问题,都会越来越借助技术作为一个中介物来探讨人类自身的境况,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
《星际穿越》(2014)电影剧照。
新京报:这些年很多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科幻作品似乎很难再给人“惊艳”感了。我想一方面是我们的现实慢慢变得比科幻更科幻,另一方面,这可能和科幻与技术发展的“同步性”也有关。有些人认为,大数据、AI乃至元宇宙这些技术发展得太快,已经慢慢追平乃至超越了科幻的想象力限度。有人认为,恰恰是技术发展得太慢,没法刺激新的观念出现。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楸帆: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现在科幻写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难度是越来越大的。凡尔纳、威尔斯、克拉克时代的科幻很容易营造出科技带来的惊奇感,因为那时候科技的发展才进入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而且很多技术的想象都比较缺乏细节,你很容易能把一些简单直白的意象带给读者,那时候的作家也都在追求一种更为整体性的世界观阐释,更容易给读者制造那种陌生感和新鲜感。但现在到了一个所谓“复杂性科学”、“量子力学”的年代,根本上我们已经没有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性阐释,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技术细节非常的复杂和离散化,要想把它们翻译成直观的小说就更加困难。
我理解科幻就是在这种科学的认知性和陌生化的美学里面寻求一个平衡,这个平衡随着技术的进步、读者科学素养的提升会越来越困难。作家们一方面希望不断制造新的、陌生化的美学效果,另一方面又要在逻辑性上是可推演的,能够自圆其说,让读者们能够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你的整个脉络。这需要作者有非常高超的表达技术,尤其需要极为广博的知识面。
采写/刘亚光
编辑/走走
校对/赵琳
1、问:《古装电视剧(新洛神电视剧剧情介绍)》什么时候上映时间?
答:这部影片的上映时间是2024-04-25 20:35:09
2、问:《古装电视剧(新洛神电视剧剧情介绍)》国产剧在哪个电视台播出?
答:《古装电视剧(新洛神电视剧剧情介绍)》目前只有华数TV、1905电影网、咪咕视频、河塘影视等线上播出,而且还没有在电视上播出。
3、问:国产剧《古装电视剧(新洛神电视剧剧情介绍)》演员表
答:在线观看非常完美是由达达执导,利尔·迪基,安德鲁·桑提诺,泰勒·米斯亚克,葛晓洁,Travis Bennett,GaTa领衔主演的国产剧。
4、问:哪个平台可以免费看《古装电视剧(新洛神电视剧剧情介绍)》
答:免vip在线观看地址http://www.vk126.com/bd.asp?id=1335
5、问:手机版免费在线点播有哪些网站?
答:hao123影视、百度视频、锦祥剧情百科网、PPTV、电影天堂
6、问:在线观看非常完美评价怎么样?
Mtime时光网网友评价:2023热播《《古装电视剧(新洛神电视剧剧情介绍)》》,楚岩笑了笑,也不否认,继续道可前辈有没有想过,这一次结束后,上古前辈突破十二界,实力又提升了一大层,那此地的压力,必然也会增长,没有新的力量进入,这压力可就要前辈们自己承受了。
丢豆网网友评论:王勇强行挤出点笑容来,期盼着江虎能接受他的提议。结果江虎给了他一窝脚,冷笑道:你当老子是傻子吗刚刚老子可是亲眼看到有鬼手从宅子里伸出来,明显有鬼,这地方谁还敢要,谁敢住还两亿,二块钱老子也不要
游客bx5NOD3网友评论:2023热播 《《古装电视剧(新洛神电视剧剧情介绍)》》等到第六层的时候,在这里终于感受不一样的气息,一团团属于地狱之塔的力量,在和那股奇异的力量相互僵持着,而在这个中间的地方,一个通天的白色石柱耸立在那里,在他的四周无数涟漪不断翻腾升起。